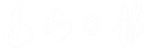由重庆首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西藏司瑶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藏地心迹》,改编自重庆知名作家周鹏程的同名长篇报告文学,以重庆援藏工作者为原型,聚焦援藏群体,医疗援建、教育帮扶、家国情怀等多元主题。用真实可感的电影镜头语言再现援藏工作者在雪域高原克服重重困难,无私奉献,既展现国家援藏政策的丰硕成果,也传递汉藏同胞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影片开始,在风景宜人的草原上,主人公马东医生正在用无人机拍摄风景,这一天应该是马医生休息的日子。突然,他通过无人机的拍摄发现几位藏族同胞驾驶的农用车陷进了泥潭,而车上有一个受伤的男孩。马东立即驾车将受伤的男孩送到医院并亲自为男孩进行了手术,男孩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他的右手因为神经损伤导致无法再动。男孩叫扎西,马东通过扎西的同学了解到他是为了保护被狼追赶的马鹿而跌下悬崖,马鹿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马东被扎西无畏的勇气深深感动,于是他将扎西的英勇事迹发布到了网络上,不承想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反响。
事情却伴随着扎西术后的苏醒发生了转变,当扎西得知右手无法正常活动时,这个勇敢的小男孩陷入叛逆、自闭的创伤后遗症。这是因为扎西一家人与国旗之间有着不解之缘。从扎西的爷爷那辈开始就是升旗手,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扎西满怀崇敬地成为了学校一名光荣的升旗手。然而,手臂受伤的扎西无法再担任升旗手,就连正常的生活也陷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境之中。马东和援藏医疗队毫不犹豫地竭尽全力帮助扎西,力求让他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
在帮助扎西的过程中,马东通过藏族护士卓玛逐渐了解到同为援藏医生的父亲马致远在昌都的一桩桩感人至深的事迹,以及父亲因高原缺氧导致心脏病复发倒在救助藏族同胞的路上,再也没有醒过来,父亲的临终遗言是:遗憾自己没能救助更多的人。当马东得知父亲牺牲的真相,那深沉似海的父爱及医者仁心的责任感,如同一把钥匙,解开了马东内心深处多年来对父亲抱怨的心结。马东觉得父亲没有陪伴自己成长中很多重要的阶段,但这一刻终于和最崇拜的父亲和解,他也完成了自己内心的救赎,更坚定了他继续完成父亲没有完成的遗志的信念和决心,将整部电影推至高潮。这种接力赓续,不正是三十年来,一批又一批巴渝儿女前赴后继地奔赴“雪域山城”昌都,为昌都建设奉献自己力量的映照吗?电影对人物塑造的基调很熨帖,没有假大空,宏大叙事与个人价值交融,深挖人性的多个侧面,于幽微处凿开人性温柔的光。让赵志盟饰演的马东更张弛有致,更丰沛立体,更真实,也体现了历史洪流中个人的成长和众志成城的力量。
《藏地心迹》从报告文学到影视的转化,还有一个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去主旋律电影的个人英雄化叙事的中心化。驻地医生、学校老师、援藏干部等多个角色都是由原型本色出演,这既是拍摄手法上的一次大胆尝试,更是主创团队力求用“真”打动观众。没有流量明星的加持,没有一味个人英雄主义,也没有霸道总裁和大女主,甚至那些夹杂着方音的台词最接地气,才是生活本身的流量密码,最朴素的表达直击人心。
戏剧冲突的处理上也是匠心独运,马东医生和已经故去的父亲之间,受伤后的扎西对周围事物的敏感和自己的封闭……这些冲突都不是从主角视角去俯视,而是通过反向视角。比如:藏族姑娘卓玛和马东父亲的忘年友谊,从而使卓玛也走进医疗行业,才让她有机会认识马东,也才让马东有机会知道父亲牺牲的真相;扎西本是被援助的对象,由于创伤后遗症让他变得敏感而叛逆,但正是通过扎西的视角看到所有人为他默默付出,让他重新燃起希望,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学会了单手升旗,在援藏干部的悉心关怀下渐渐走出创伤后的阴影,并且愿意同马东医生一起前往重庆接受进一步治疗。
电影于2024年8月在西藏昌都开机,为了更加充分地贴近原著的真实,《藏地心迹》在拍摄早期,主创团队遍访西藏,并对其中的多个拍摄方案进行反复甄别遴选,最终确定把昌都的类乌齐县作为拍摄主场景。类乌齐县,被称为“西藏小瑞士”,以其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溪流和高山草甸景观著称,为影片提供了优美的自然背景;绝美风景和深厚文化,为电影的故事叙述提供了浓郁唯美的艺术气场支撑。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重庆援藏30年,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藏地心迹》的上映不仅呼应了重庆援藏30年等核心属性,也坚定了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电影紧扣援藏题材这一深刻母题,聚焦援藏工作者群体,覆盖医者仁心、教育奉献、家国情怀等多元主题,电影整体的艺术表达非常新颖,摄影师的镜头在重庆和昌都闪转腾挪,飞驰的轻轨,无垠的草原……捕捉了这两座不同地域“山城”的城市风貌和人民生活。加上主创团队对构图与色彩的精心搭配,增强了观众的视觉冲击力,美妙空灵的音乐,让观众沉浸式地在光影之旅中感受一次心灵的洗礼。
藏族同胞每次给援藏工作者献上的哈达,是汉藏一家亲、民族大团结纽带的象征;影片中多次出现了雪山,蜿蜒曲折的山路,山隐喻时间的见证者,见证不惧困难的藏族同胞和援藏工作者在缺氧的高原建造的美丽家园,见证国家援藏战略为西藏带来的巨大发展变化。
作为重庆首部援藏题材电影,《藏地心迹》首映后引发观众热议,这不啻是对主创团队最好的褒奖。该片还获得了国家电影局电影精品专项资金资助。
电影还有一个最令人动容之处在于它对“距离”的重新定义。重庆距离昌都约2000公里,在交通基础设施极为落后的1995年,从重庆到昌都的旅程是一次非常艰苦和漫长的“远征”。我读师范时的一位同学,从2016年参加援藏教育队,一坚持就是9年,他离开重庆的时候女儿还在读小学,如今女儿都高三了。被岁月雕刻的不仅仅是鬓角的银发,更是每一位援藏工作者刻在骨子里的执着,坚韧,初心情怀。
当影片落幕,我们恍然醒悟:山海从来不是爱的阻隔,而是爱的见证者。那些以为会被距离阻隔的情感,反而因跨越距离而变得弥足珍贵。《藏地心迹》不仅是一部电影,而且还是一封写给人类共通情感的情书,提醒我们:有一种爱,不以山海为远。
□袁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