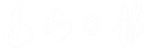回到镇上的老家,我多少有点“认床”,夜里顺应家中老人的生活节奏早早躺下,却翻来覆去,久久难以入眠。
深更半夜,模模糊糊听到厨房传来声响,一会儿是流水的哗哗声,一会儿又是锅铲碰撞的砰砰声,随后又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仿佛有人在吃面。当时我头疼欲裂,身体感觉软得像团棉花,下意识想起身查看,却又动弹不得。又迷糊了一小会儿,只听见大门“吱嘎”一声被推开了,或许是年久失修,铁门生锈,开合间满是滞涩。随即“哐当”一声,门被关上了,四周重归安静,这些声响像针线般缝进我的梦境,让我在昏沉中浮浮沉沉。
早上七点过,窗外天光大亮,明晃晃的,照得我眼睛发疼,我终于起了床,准备给一家人煮面,这才发现母亲不见踪影。原来,深更半夜起床弄早饭吃,然后出门的,正是母亲。我急忙拨通母亲的电话,电话那头,她语气平静:“做小工哩。”我又追问她几点起的,早饭吃了啥,她轻描淡写地说:“四点多就起来了,煮了点面,就着昨天吃剩的嫩苞谷籽,将就了一顿。”
很难想象,这是一位69岁老太太的日常生活:饮食上从不讲究,一把年纪了,没想着保养身体、享享清福,反倒是把干活儿看得比什么都重。平日里,她忙完自家的零碎农活还不够,一有空还要去队上张老板那里做小工——割草、除草、掰玉米、晒玉米……凌晨四点多钟就起床做饭,五点钟出门,六点钟下地、十点钟收工,下午两点钟出工,六点钟收工,一天下来,能挣60元钱。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拼,是家里经济紧张,还是子女不孝顺?各位,误会!纯属误会!我们一大家子,日子目前还算过得去:姐姐、姐夫在外打工,勤劳踏实,抚养孩子不成问题;我也有稳定的工作;父亲偶尔在街上做零工,也能挣到几百上千块钱;两位老人每年还有社保,我和姐姐也会按时给生活费,逢年过节也少不了会拿红包,所以对于我母亲的情况,我单纯地总结为:闲不住!根本闲不住!当然也劝不了!没人劝得了!
既然劝不了,那么我能做点什么呢?思来想去,那就明天一大早,我力争早点起来为母亲煮一碗稍微爽口的面条吧。于是,我把手机闹钟调到凌晨四点半,心想她吃完再出门,时间应该刚刚好。结果第二天早晨,还在睡梦中的我又听见厨房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翻身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打开瞅了一眼,果然才四点过一刻,我强行睁开睡眼,挣扎着起床去了厨房。
昏黄的灯光里,她像一尊孤独的雕像杵在洗碗槽旁,一头白发凌乱蓬松格外扎眼,后脑勺的头发拢在一起随意绾成个疙瘩,佝偻着身躯正在专心地洗着自己用过的碗筷。空气里弥漫着昨天吃剩的红汤火锅底料的鱼腥味。我心头一阵发涩,她肠胃本就不好,又是这样匆忙对付一顿。终究,我还是没能如愿认真为她煮一碗面条!
收拾完厨房,母亲走了出来,见我默默坐在餐桌旁,她小声责备:“这么早你起来干啥,不多睡一阵?”说着,便自顾自地开门,准备干活去。我没有接话,只是凑上前轻声说:“最近天这么热,就别去做工了,当心中暑。”她弓着身子,一边换鞋一边头也不抬地说:“太阳大了都收工,别人想去还不行呢,有时间就去做点小工,手头的活儿,不累,也还是可以嘞。”接着,她又挽留道:“你们要不多耍几天再回去嘛!”我告诉她,今天要回去拿孩子的体检报告,她迟疑了一下,说:“也是,快开学了,娃娃体检上学是大事。”
她出了门,顺手带了下门,但门没合上,又弹开了,我探出头去关门时,楼梯上的她听到“吱呀”声,她停下脚步,我们对视了一眼,昏暗的楼梯间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忍不住又叮嘱一遍:“天气热了,就不要做了,注意休息”,她低下头,轻轻“嗯”了一声,下了楼,楼梯间空空的,我的心也跟着空空的,这一刻我们明明这么近却又那么远。
两代人的隔阂由此显现:我们追求的是让父母安享晚年,他们渴望的是不被时代抛弃。我们想给他们舒适的养老生活,他们却害怕成为子女的累赘。这种互相关爱却彼此误解的悖论,让亲情在时空的错位中渐渐疏远。我之前一直认为成功的父母本就应该让孩子在成年之后,从原生家庭逐渐分割出来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体。可这个“分割”在时空、岁月面前,竟显得尤为残酷,我们不光完成了物理上的分割,伴随而来的精神上的鸿沟也越来越深,久而久之,我和母亲之间终究是生分成了亲戚一般的寒暄,这让我内心涌起一股悲凉。
但我也意识到,母亲不是在劳作,是在为自己修筑退路。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命存在的证明。她怕成为子女的负担,怕晚年拖累我们。于是用最笨拙的方式,在土地里攒足尊严。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翻过月台,我的母亲穿过晨雾,都是爱的姿态,却都让子女心碎。如今明白,真正的孝顺不是阻拦,是理解。不是施舍,是尊重。或许真正的孝顺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去爱他们,而是尊重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
我们这代人总想着独立自由,以为将父母安置在舒适圈里便是孝顺。却忘了他们最怕的不是劳累,而是无用。母亲与土地的关系,比任何亲情羁绊都更古老深沉。她在泥土里播种收获,获得的不仅是60元工钱,更是生命价值的确认。
下次回家时,我还会设置四点半的闹钟,或许依然赶不上为母亲煮一碗面,但至少能站在门口,看清她消失在天光里的背影。那时,我会记住,母亲的安全感扎根在黑土地里,而我的安全感,来自知道母亲正在她选择的道路上走得踏实。
这片土地给了她我们永远无法给予的活着的意义。也许亲情最深的境界,不是紧密相依,而是遥遥相望却彼此心安。就像大地永远守护着种子,却给予它自由生长的空间。
□程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