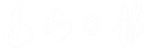“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按理说,我与这首词中所写的相思情态本是沾不上边的。但自从2018年儿子大学毕业首站工作在重庆九龙坡辖区的庆铃汽车集团,我为他在大渡口九宫庙附近购置了一处房产后,便从此与重庆结下了缘分。后来,儿子离开重庆去了成都发展,便很少再回到这里;我却因此常往重庆跑——“山城”的坡、“雾都”的雨、“火锅”的辣、“棒棒”的韧、“3D魔幻城”的奇、“红岩”的魂,这些词汇渐渐刻进生活;与这座城的联结,也在千丝万缕中变深,成了戒不掉的情结。
曾几何时,大渡口、九龙坡,乃至整个大重庆,与我这个四川人似乎并无关联;可如今,我却处处牵挂着大渡口、九龙坡,牵挂着重庆。在重庆,像我这样“蜀来渝往”的大竹人还有很多——商界的刘达平在这里投资兴业,为城市注入活力;文化界的王明凯、张天国用笔墨描绘重庆山水,传递巴渝韵味;更多普通的大竹人,在街头巷尾勤劳打拼。他们把大竹的耿直带到重庆,也把重庆的活力带回故乡,成了“川渝一家亲”最鲜活的诠释。
正所谓“渝来蜀往,大美竹乡”。我的家乡在四川大竹,很多年前,当地就流传过一句口号:“要把大竹打造成重庆的后花园。”大竹的确配得上这份期待——这里山美、水美,人民勤劳聪慧,大竹的妹子,是叫得响当当的漂亮,重庆人跑到大竹来找对象的,屡见不鲜,能娶到大竹妹子作老婆的重庆人,大多能幸福一辈子。五峰山的竹海,风过时绿波荡漾;百岛湖的晨雾,日出时如梦似幻;欢喜坪的草甸,盛夏时铺锦叠翠;广子村的炊烟,傍晚时袅袅升起;清河古镇的青石板路,雨后泛着光,述说着岁月的故事。五月左右,我去五峰山脚下的农家乐吃饭,邻桌是一家重庆人——爸爸抱着娃在竹林里掰竹笋,妈妈举着手机拍随风摇曳的竹梢,老人坐在竹椅上跟老板唠嗑:“你们这竹蒸笼蒸的肉,比重庆馆子的还香!”老板笑着答:“下次带朋友来,我给你们留最嫩的竹荪!”每逢周末,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重庆牌照的车辆穿行在大竹的乡道上,人们在这里呼吸清新空气、品尝地道农家菜、享受悠闲慢生活。如今“轻旅游・微度假”模式在大竹悄然兴起,重庆的休闲人群如“润物细无声”般向这里汇聚,川渝两地的千年情结,也在这样的往来中再度紧密相连。
如果说大竹的山水是“后花园”的底色,那么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人,便是底色里最亮眼的纹路——在重庆颇具名气的范绍增,正是从大竹清河古镇走出的传奇。他修建的范公馆、宅邸,至今还有部分保存完好。范绍增也就是系列电视剧《哈儿师长》中“樊哈儿”的原型,其外号叫“范哈儿”,拍电视时为避免侵权纠纷,才改“范”为“樊”。去年,我去沙坪坝山洞街道办事,特意绕到平正村的范公馆——青灰瓦上长着几丛瓦松,木窗棂的雕花还能看清,门口的石碑刻着他“自掏腰包招兵抗日”的故事。风吹过屋檐,倒像能听见当年他跟部下说“绝不拉稀摆带”的豪气。真实的范绍增,一生本就充满传奇:13岁参加袍哥,早年混过赌场、当过土匪,后来被招安进入川军;他以袍哥义气为部队纽带,部下打仗肯拼命,自己也因作战勇猛不断晋升,先后任川军旅长、师长。抗战期间,他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八十八军军长,回大竹招兵买马时,还自掏腰包购置军火;率部出川后,在抗日战场上战功赫赫,1942年5月,其部队先是击毙日军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酒井中将,次日又击伤日军第四十师团少将旅团长河野,在抗战史册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烽火岁月里,范绍增的选择与担当,正是千万川军将士“铁血卫国”的缩影。他代表的“耿直、仗义、血性,绝不拉稀摆带”的精神,早已成了川军、川人的精神图腾,在国人心中立起了一座丰碑。这座丰碑上,刻着烽火岁月里的铁血担当——抗战时期,300余万川军将士出川抗日,装备简陋,却冲锋不退,在台儿庄、淞沪、长沙等战场筑起血肉长城;也彰显了危难时刻的大义凛然——无论是抗震救灾时“川人从不负国,国人亦不负川”的双向奔赴,还是日常里“巴适”表象下藏着的坚韧乐观。这份丰碑的分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更有烟火气里的生命力,任凭时光流转,始终清晰矗立,成为刻在民族记忆里的精神坐标。而作为川人,我也始终觉得,自己的血液里同样流淌着这份耿直与血性。
每次驾车往返于大竹与重庆的高速公路,看着沿途川渝牌照的车辆交织往来,再想到西渝高铁将过境大竹、两年后正式通车的消息,便愈发真切感受到大竹与重庆这对“近邻”正加速向“同城”靠拢——届时从大竹出发,坐高铁半小时就能抵达重庆主城,通勤比不少重庆跨区出行还要便捷。川渝两地本就同属巴蜀文化圈,地理上山水相依,人文上血脉相融,这样的“同城化”不是单向的奔赴,而是川渝人骨子里的双向奔赴——你看高铁在山间穿梭,人们在两地间往返,江水在两岸间奔流,每一处都是“川渝一家亲”的真实写照。滚滚长江,奔流不息。它从我的家乡大竹以溪流的形式,入铜钵河、经州河、绕渠江、汇入嘉陵江,在朝天门入口,一路蜿蜒至我牵挂的山城重庆。我这“蜀来渝往”的步履,不过是千百年来巴蜀大地血脉流动的一丝微澜。我站在马桑溪大桥上远望,只见长江水汤汤东流,一如千百年前的模样。我知道,浪花虽已淘尽英雄,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承袭着那股“绝不拉稀摆带”的豪气与耿直,在新时代里书写着新的传奇。大美竹乡,既是重庆人休憩身心的“后花园”,也是川渝协同发展中活力涌动的“补给站”。
此情此意,正如那共饮的一江春水,绵延不绝。这,也正是“渝来蜀往,大美竹乡”的深情所在。
□吴华